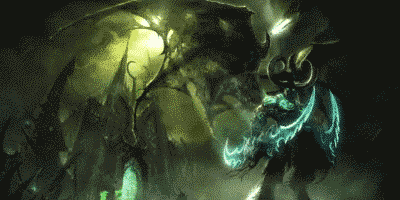4月28日下午,病毒学家张永振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T2航站楼。
本来团队成员陈燕玫准备开车来接他,但她没有出现。这位研究员正被关在张教授团队的实验室里。张教授的其他学生,则被拦在实验室门外。
在此前的25号那天,实验室所在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名副院长,带着保卫科长及几名中心干部,通知所有工作人员有急事儿,要开个会。
领导在会上宣布,这里的实验室要进行改造装修,必须在2天内全部搬离。在现场的一名研究员说:
整个通气会一共开了1分钟。领导们随后匆匆离开,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
一个超过500平方米的实验室,器材、设备、冰箱、样本数量都没统计的实验室,要如何在2天内搬完,大家不知道。
陈燕玫在钉钉上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要他们暂时搬去另外一名教授那里。
陈燕玫有点蒙。且不说2天的时间太短,他们做的是病毒研究,新的实验场所符不符合要求,是不是应该提前询问一下当事人的意见?
已经没人回复她了。
恰逢张永振出差广州,陈燕玫决定老师回来之前,都住在实验室里。出乎意料,两天的期限一到,实验室大门立即被关闭了。
出差回到上海的张永振开车来到实验室门口。和保安对话无果后,这位马上60岁的著名病毒学家做了个决定:
睡在实验室门口。一堆纸壳,一床被子,一个枕头。纸壳是学生们在中心里收集的,被子和褥子是陈燕玫从实验室楼的缝隙递出来的。
夜色中,只有实验楼外昏暗的灯光闪烁。保安们用手机刷着抖音,声音很大。上海开始下起了雨,张永振想向有遮挡的方向靠近一点,也不不容易。
那晚,他的被子湿掉了。
实验室门口,张永振躺了3天2夜。期间,公卫中心的领导来过一次,让张永振回去,别躺了,其他什么也没说。
舆论发酵后,4月30日晚,张永振拿回了门禁卡。5月1日早上,学生们也回到了实验室。
我问这位2020年《Nature》杂志年度自然科学领域十大人物,躺实验室门口时想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说一夜难眠:
但没关系,这几年也都睡得不好。1
能成为《Nature》杂志年度十大自然科学领域人物,还得从四年前另一个夜晚说起。
2020年1月5日凌晨2点,正准备睡觉的张永振接到学生陈燕玫从北京昌平打来的电话。她告知张永振,武汉送来的样本数据经过分析:
发现了类冠状病毒的序列。张永振一直在关注肺炎。他曾经参加抗击非典疫情,一直认为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一定会成为人类世界的大威胁。
因此,2014年前后,张永振就和武汉疾控中心、武汉中心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时,对方就会将样本送往张永振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12月中旬,张永振就听说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但彼时恰逢妻子去世,张永振还没精力关注。
之后,上海中山医院又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腹泻,张永振被指定进行研判。因此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和新冠病毒擦肩而过。
时间到了1月3号,刚过完生日的张永振收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生物样本,及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医生们采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样本。
两名助手宋志刚和吴凡开始进入p3实验室处理样本和核酸。其他人开始建立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北京的陈燕玫,则负责进行数据分析。
5号的凌晨,他接到了陈燕玫的电话。那天凌晨,张永振让陈燕玫别睡了,连夜把全部基因序列都做出来,并让一名在北京的同学赶去给陈燕玫帮忙。
第二天早上,张永振团队就获得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分析后大家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过的全新病毒。
张永振立刻给自己的合作伙伴,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打去一个电话,询问病患情况。结合合作伙伴的反馈,张永振得出了判断:
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经呼吸道传播;
致病性和公共卫生风险高于高致病性禽流感。同时他建议,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临床上使用抗病毒治疗。
一夜没睡的张永振马上上报。他找到时任上海市公卫中心的负责人朱同玉,告诉他这件事非同小可,请求他马上通过最高渠道上报。
而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疾控和卫生部门进行汇报。
这一天,他也为新病毒注册了GenBank。
次日,张永振回到北京,为刚刚去世的妻子选好墓地,又将总结好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投给了《Nature》。
1月8号,张永振亲自去了一趟武汉,到武汉中心医院和一线医生了解情况。这更加深了他的判断和忧虑。
9号,他接到了《Nature》编辑打来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公开序列并发表文章预印版。张永振怕被人说抢发论文,拒绝了预印版。公开序列则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
张永振想了很久。11号,他临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前,再次接到合作伙伴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香港等地已经出现了疑似病例,希望他能尽快公开序列。
张永振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来思考,最终决定授权合作对象在网络上公开全部序列。
这一分钟,挽救了这座星球上无数人的生命。
后来推动研发出新冠mRNA疫苗的德州大学教授麦克米伦这样评价张永振的工作:
公布基因组序列的那一刻,发令枪就响了。2
2020年2月,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收到一份来自上海公卫中心的商调函,希望将该单位的研究员张永振,调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张永振2018年就在公卫中心兼职工作了。根据当时的合作协议,张永振将和公卫中心展开合作,为期5年。
公卫中心当时的领导朱同玉和卢洪洲非常看重张永振的工作。尽管他没有院士这种闪耀的头衔,但没辜负两位领导的期望——从2018年到2020年,张教授带领团队以公卫中心的名义,在《Cell》和《Nature》上各发表了3篇文章。
2020年,张永振决定接受两位领导邀请,前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当年10月,张永振出现在上海公卫中心拟录用的公示名单中。国家疾控中心也办理了张永振教授的调离手续。
彼时张永振受到了公卫中心的礼遇。主任朱同玉将自己办公室让出来给张永振。无论是实验室改造,还是招收学生,申请宿舍,张永振都得到全力支持。
但两位领导从公卫中心离职后,张永振觉得气氛有一些微妙了。
他的人事关系被卡在了半空,公卫中心迟迟不为他办理入职。学生们发现自己的实验开始变得并不顺利。申请材料、宿舍等小事开始屡屡受阻。
就合作协议到期时间及劳务费等问题,公卫中心也和张永振产生了争议。公卫中心认为协议开始于2017年10月,到2022年10月就已经终止了。现任领导说:
张永振就是赖着不走。张永振却认为,协议实际签署于2018年3月,实际到期时间应该是2023年的3月:
我2018年4月才办的银行卡,用来收劳务费。当初的协议,双方都没有写明日期。
公卫中心依旧按2022年10月的日期,在此之后停了张永振的OA权限。随后,上海公卫中心向国家疾控中心退回了张永振的档案,但档案被拒收了。
因为到期时间的争议,协议中规定的劳务及研究费用也停发。张永振认为公卫中心欠了团队近千万劳务费和实验经费。
抛开合作协议额,张永振认为自己明明是事业编制,人事调动是公对公行为。结果干了几十年,快60岁了:
编制莫名其妙没了。因为曾患有甲状腺癌,张永振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也一直拖着没去医院做手术。因为编制没了,他的医保停了,社保也停。
至于实验室改造,按照张永振的说法,实验室根本不需要改造,因为整个实验室落成是在2020年,这才过去几年?
在他的实验室同一栋楼里,还有一个P3(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刚刚才通过国家认可委专家现场评审测试。这又需要改造什么?
一句“赖着不走”,让张永振心寒。他说如果不是档案和劳务费等问题,他早想离开这里。但这些问题,一直没人出面和他沟通。
3
张永振很简朴。
一条已经磨掉色的皮带,一块戴了10年的手表,一双已经磨掉底的皮鞋。
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每天张永振都会在8点前赶到实验室,然后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再回家。
每一个学生的实验,张永振都会亲自把关。学生们说,在张教授的实验室,除了春节:
没有休假、没有双休。按理说,这种远比996强度还大的实验室,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呆得住。
但奇怪的是,张永振似乎有种独特的魅力。陈燕玫是中山大学为了吸引他帮他招收的研究生,一路跟着他从国家疾控中心到了上海。
宋志刚原本是公卫中心的正式员工,却跟着一个“兼职”教授走到最后。
还有很多学生来自复旦。这些天,这些学生都一直跟陪在张永振左右。
有位复旦生命科学院的在读博士本来不打算读硕博的,直到遇到张教授。
这位博士说,很多团队都是什么火做什么。但像张永振这样一直在病毒学领域深耕多年的,非常少。
和很多教授不一样,张永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本科是石河子农学院,学的畜牧专业。毕业后又在新疆兵团做了6年的行政工作,甚至管过拖拉机。
1998年,张永振博士毕业。但直到2005年才发出自己第一篇SC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实验室连台像样的PCR机器都没有:
唯一一台进口PCR仪器,还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但张永振之后在全球病毒学界享有盛誉。他曾带着团队发现了5500多种新病毒,多次在全球顶级期刊上表论文。国家疾控中心评价他的工作:
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主要空缺,改变了病毒学的传统观念。尽管没有任何留洋经历,但张永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牛津英汉词典。
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当初《Nature》将他评选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时,他曾有过一段不能明言的抗争,在个人荣誉和国家形象面前,坚定选择了后者。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国时,在澳大利亚看到现代化畜牧业的震撼。当地一双皮鞋也要几十澳元。而他当时的工资,也就100块钱。后来他才知道,一个剪羊毛的女工:
一天就能挣80。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记得这种差距,有一种强烈想追上发达国家的迫切感。
张永振说,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科研工作被耽误。
他躺在实验室门口的照片,像一幅油画。江湖夜雨,昏暗的灯光,若无其事的保安,拍照的学生,及躺在纸板上的张永振。
他要守护的,是他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和样本,作为病毒实验室,室内要处于负压。
一旦压力增大,内部气体泄露出来,那就要出大问题了。
赞(38)